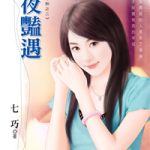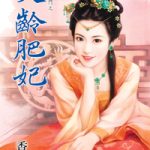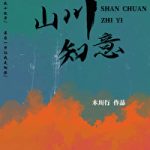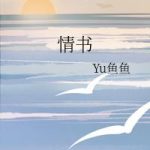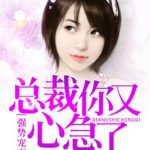作者有話要說:
楊康初次見到歐陽克時,那人輕裘緩帶,眉眼含笑,端得一副翩翩濁世佳公子的氣派,心裏便在想——爹爹請來的這些個武功好手裏,這人瞧着最是順眼,當下就起了結交之心。
彼時他自己也是個标準的纨绔子弟,比之大金國同輩的富貴王孫,也就打架的本事強上一些,沒什麽其他值得稱道的地方。殊不知連這唯一的優點白駝山少主也是不放在眼裏的,之所以耐煩應付他,一方面是因為歐陽克身趙王府的客卿,要給王府主人完顏洪烈面子,另一方面,卻是因為楊康長得還不錯,遠不是梁子翁、侯通海這等歪瓜裂棗可比。
因而等到楊康自以為“禮賢下士”地去結交歐陽克的時候他才發現,原來人家壓根沒半分“下”的自覺,反而很欠揍地認為,他堂堂白駝山少主,跑來陪小王爺敷衍消遣才是屈尊降貴。
差點沒把楊康氣歪了鼻子。
心裏一個不忿,臉上倒還沉得住氣,皮笑肉不笑地跟歐陽公子打兩聲招呼,便出了王府上街找樂子去了。
若是早知道他這一回出門會招來怎樣的禍事,他寧可那一整天都陪母親坐在那件破屋子裏,聽母親講兔子腿斷了該怎麽上藥怎麽接骨。
可惜千金難買早知道。而被他遷怒的罪魁禍首歐陽克,此時卻還懶洋洋地在客房喝酒吃菜外加調戲他的姬妾。
也難怪歐陽公子,好好的二十四個美貌弟子,平素就算拈酸吃醋也別有一番味道,莫名在道上死了兩個,怎不叫其他人心下黯然?除了拍胸脯跟餘下弟子保證一定會給那二人報仇,就只有打疊精神想法子哄她們開心。
既跟了他歐陽克,他總要擔負起她們的身家性命。
他一邊撫摸姬妾光潔白皙的臉蛋,一邊将自己想得大義凜然,正美滋滋地不知所以,全然沒想到他方才面對楊康時自以為藏得高明的不耐早給楊康看了出來。
他卻不知,論格調檔次,他和楊康本來半斤八兩,誰也沒比誰高,奈何盡管兩人一丘之貉都不是什麽好貨色,歐陽克平素接觸的都是對他叔父大肆巴結的谄媚之人,楊康好歹還碰上過幾個地位在他之上的,因而比他歐陽克懂看人臉色得多。
若歐陽克有半分楊康此時的能耐,豈會在半年後如此狼狽地死在一把破槍頭下?
但此時的歐陽克尚未能知後事。而此時的楊康,自然也不能。
楊康此刻很有些頭痛。
不過是想出來找個樂子,誰料居然見了血?想起三個月前自己胡鬧生事,連累得爹爹在朝堂上被金帝訓斥,更很有些惴惴不安。
先前見那賣藝老漢一掌把自己随從打暈,他已有些不安,因而二話不說,想要上馬走人,存心想要此事不了了之。至于背後怎麽被人咒罵,那都不必放在心上。
然則他見多了争名逐利之輩,卻忘了有人厚顏無恥,自也有人有心氣血性。世事從不是他待如何便能如何。待到郭靖與王處一先後出手,這一次胡鬧便再不可能簡單收場。
但那時他尚未想到,這一次的胡鬧非但不只是不能簡單收場,甚至演變成了他一輩子除死之外最大的變故。
若是早知道,穆念慈那繡鞋還便還了,最多也就是事後被那些個堂兄叔伯笑話幾句罷了。
又有什麽大不了。
可惜當時不懂事,舍不得面子。
幾個月後每每想到這日的比武招親,他想得最多的也就是——
還繡鞋便還繡鞋,賠不是便賠不是,哪怕真娶了穆念慈也好。臉皮面子算什麽東西,心氣血性值多少錢?趁早扔了才好。
要是打一開始便不要臉到底,便涼薄到底,大約以後也不至家破人亡。
後來歐陽克便嘲笑他說,小王爺聰明臉蛋笨肚腸,反思往日,後悔的居然是自己太要臉。
楊康冷笑一聲,不恥下問:“那我該如何想才是?”
歐陽克不答反問:“小王爺原本怎麽想的?”
原本怎麽想的?
楊康怔了怔,只覺一張臉又青又白,再說不出話來。
即令沒有他母親和楊鐵心那一檔子事,他真的騙得穆易穆念慈在老家等他一輩子,他任性妄為難道就能有個好收場?
他當時沒留下郭靖和王處一殺人滅口,反而在事後命人買走了全中都的藥材。
便是他萬年倒黴,難得心想事成一次,真的令王處一殘廢終身,他又打算如何應對丘處機的怒火?
做起事來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亂七八糟的把柄多如亂麻,也難怪歐陽克笑話他大愚若智。
也不知哪個缺心眼的禍害第一個贊他聰明,成心想害死他。
後來他果真死在自作聰明下。心想歐陽克若是死後變鬼,尚可找他索命,他楊康孤零零地死了,卻連恨都不知該恨何人。
便如此刻的他,傻愣愣跪在包惜弱身前。腦子裏一片空白,心中一肚子怨憤,卻不知該怪誰。
怪他親爹還是親媽?怪他養父還是師父?
怪到最後,不如還是怪他自己吧。
若是好好聽了他媽的話,哪怕随口敷衍楊鐵心一句爹爹,他們未必便這樣絕望,以至存了必死之心吧?
他分明最擅花言巧語,卻總在關鍵時刻掉鏈子。明明早知道母親是怎樣軟弱的人,便是只看她的眼睛都能知道她方才有多恍惚,只怕連她到底身在夢中還是現實,是在地府還是人間都搞不清楚,他為什麽偏不肯順着她?
她總是慣着他寵着他,看着他胡鬧毫無辦法,他卻從不肯好好聽她的話。
連她死前最後一個念想都不肯給她,不孝至極。
後來他連逼死父母的仇人都能滿口的“爹爹”,卻再沒有喊楊鐵心一聲“爹”的機會。
分明早已錯過,卻還要自欺欺人,妄想自己若能不像待母親那樣,凡事順着別人一點,便能抓住早就不在了的人。
殊不知大錯鑄成,在歧路上行了太遠,終不能再回頭。